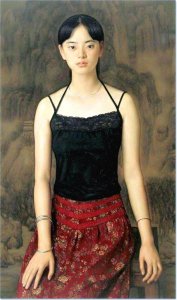真情写作 | [日本]黑孩《写作从伤感出发》(散文)
真情写作 | [日本]黑孩《写作从伤感出发》(散文)

转载请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


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青年文学》编辑。文学创作开始于1986年,1992年留学日本,现定居日本。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说集 《父亲和他的情人》(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傻马驹》 ( 四川文艺出版社 )。散文集 《夕阳又在西逝》(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女人最后的华丽》(文汇出版社)、《故乡在路上》 ( 安徽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秋下一心愁》 ( 春风文艺出版社 )、《樱花情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惠比寿花园广场》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收获》《花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作品被《小说选刊》《思南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

写作从伤感出发
文 / [日本]黑孩
今天在朋友圈上看到一句话:我一直以为回锅肉就是炒两遍的肉,回锅嘛。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个好笑的表情。不由得笑起来,觉得这位朋友真是太可爱了。类似的感觉我也有。比如我经常会想,东京的狗如果跟北京的狗见了面,会不会像老虎看狮子。还有,家里养的猫能不能理解流浪猫。想来想去都得不出答案,说起来很伤感。
我在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里写过我家里的一些事。爸爸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却都用来喝酒抽烟。六个孩子里,大姐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生的。二姐、三姐和四姐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哥哥是工农兵大学生。我是恢复大学考试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妈妈白班晚班地打各种工,赚来的钱依然不够全家的开支。关于童年的记忆灰蓬蓬的。一生中最无法忘却的是学费的事。每次交学费之前,妈妈都要我去邻居家借钱。妈妈之所以选定不满十岁的我去借钱,我想跟我的年龄有关。妈妈肯定认为人们难以拒绝一位小孩子的要求。妈妈这样教我:“你去借钱的时候,你就说我爸22号发工资,22号那天肯定还钱。”我至今都记着这句话。对我来说,22号是我永远无法忘却的极其伤感的一个日子,连数字本身都浸透着哀伤。
说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熬不住种地之苦,二姐一次接一次地从普蓝店跑回家里。二姐坐火车回家,回家的时间,正好赶上家里人围着饭桌吃午饭。二姐不敲门,而是特地绕到后院敲窗玻璃。我家那时住一楼,二姐敲窗玻璃,我们一同看窗。一看到二姐,妈妈的手就会控制不住抖起来。第二天,妈妈送二姐回农村的时候说:“城里没有你的户口,没有户口就拿不到口粮。你不在农村待着的话,连农村的口粮也拿不到了。这一次回去,你要尽可能待得时间长一点。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二姐一直哭,对妈妈说,农村的太阳特别毒,烤得脸颊痛。还说太阳地里种水稻,腰痛得直不起来。妈妈说:“你得学会忍啊。你要忍到你被抽调回城。”为了口粮,妈妈逼着二姐回农村。妈妈跟二姐说再见的时候,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地喊:“你要学得省心点儿。”我还记得那时的二姐,披散着乱发,一脸的泪水,从头到尾都是愁眉苦脸的。但同样是知青的三姐和四姐为什么跟二姐不一样呢?不到农村放假的时候绝不回家,绝对不给妈妈“添麻烦”。因为是这个原因,我至今也不知道她们的下放地点叫什么名字。但三姐跟妈妈说过的事我却记得很鲜明。意思就是太阳很毒,昏头涨脑地插完秧,腰痛得只能爬着回田埂。对农耕怀有恐惧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二姐、三姐和四姐这样的经历,至今也没有见识过农村,不熟悉土地,对农村的想象除了一大片绿油油,还是一大片绿油油,是田园式的。我的世界一直是一张写字台,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出版社,到大学院,再到出版社。结果我对文字特别敏感,几乎可以说是病态。环境与感受,就像一根很长很长的线被扯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多少年后讲起她的几个孩子时,妈妈总会叹一口很长的气说:“小孩子真是从小看大。老二从小就不省心,尿床尿到上中学。所以她去农村的那几年,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折腾在火车票上了。”而我呢,从小就离家出走,对故乡和人生有强烈的幻灭感,所以讲到我的时候,妈妈会后悔地摇着头说:“早知道读书让你成天到晚地想死想活,我就不会让你上大学,而是让你去工厂做工了。”
我知道,这是伤感。妈妈的伤感。迷惘也好,爱也罢,其实都是伤感。来日本后我经常去温泉。白昼去小街散步,看一幢幢旅馆附近冒出的一缕缕热气像白色的烟雾,感觉里面藏着很多个故事。也许不懂得人生的人,才会感到真正单纯的幸福。也许懂得死的意义的人,才会活得更加坦然。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不太靠谱,但伤感确是感受生活的一种能力。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小时候,家里的厕所跟房间隔着一条很长的走廊,黑漆漆的。窗户对着后院。大概是怕“鬼”吧,一直到上中学为止,夜里去厕所的时候,我总是叫醒妈妈陪着我一起去。有一次从厕所里出来,我爬上床,准备睡觉,妈妈说:“什么时候你去厕所不再需要我陪了,我就该休息了。”上了中学,一个人去厕所不害怕了,发现走廊比想象的狭窄,而窗户比想象的要高,只是非常小,根本容不下一个人的脑袋,于是觉得有点儿虚幻,竟在厕所里叹息起来。忽然觉得自己的胆子小得有点儿惨。寂寞从心底迸发出来,不由得对妈妈充满了谢意。
稍微懂一点儿事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妈妈在厨房偷偷地擦眼泪。我走过去拉着妈妈的手,伤感地对妈妈说:“妈妈,不要哭了,我会长大,我会把你现在的苦处都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理解你。”
所以我的创作是从伤感出发的。我觉得创作就是邂逅,来自生活。虽然不变的是已经逝去的童年的环境,但童年的环境却给了我支配自身命运的某种力量。如今想起已经死去的妈妈,我觉得非常寂寞。太寂寞了!童年的背景变得虚幻。妈妈恍如一缕忧伤的黑发在天空飘忽,于是白云看起来更白,连云间的霞光看起来都像是飘忽的头发了。穿一件藏青色的上衣,留着齐耳的短发,长得十分美丽的妈妈是光景,而这样的光景已经成了过去的梦了。我一直以为藏青色是最能表现清洁感的颜色,并酷爱藏青色的衣服。我在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里写道:“我对妈妈的伤感的记忆,常常潮水般涌到眼前,它们具有着形状和味道,好像两臂间的投入,两个唇齿间的亲吻。”
我是1992年2月到日本的。完全是随波逐流。那时国门打开不久,一首歌红遍全国,其中的歌词是:“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边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我也一样。刚好我翻译的书的作者是大学教授,他发邀请,希望我能到他所就职的大学留学。不管怎么说,从大学的时候开始,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日本文学,知道樱花与红叶是日本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我也知道日本武士推崇樱花,认为樱花的美,不是盛开,而是凋谢。最好的例子是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虽然我现在重新读这本书时已经流不出泪水,但我还记得当时读完这本书后所受到的巨大冲击:悲伤铺天盖地。泪水涌出来,永不休止似的。《金阁寺》是一场爆烈的美的祭典。三岛由纪夫是想通过美的毁灭的伤感,来唤起读者对现代社会的对比。而三岛由纪夫本人,无疑正是樱花一样的男人。生命在达到至极的美丽的巅峰之后,毫无留恋地结束了。他在《奔马》中写到:“就在刀刃猛然刺入腹部的瞬间,一轮红日在眼睑背面粲然升了上来。”他在45岁选择了自杀。他的死也是创作。回想起来,我那时的心情是,有朝一日可以亲眼看到金阁寺。
……试读结束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0年第8期

再说伤感
文 / [日本]黑孩
恢复写作后一共在《北京文学》发过两篇散文。除了这篇《读书写作是因为伤感》,还有一篇是2017年第2期发表的《寅次郎》。
那会儿我来日本快三十年了,虽然其间断断续续地写了点小文,但好像不算正经写作。想正经儿写点儿什么。写小说是需要技巧和控制力的,所以,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散文显然更加合适。我一直觉得散文是一种自然状态上的表达和倾诉。
这么巧,有一天跟主编杨晓升聊起写作。我记得自己说不知道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杨晓升说:“内心表达的需要啊。如果不需要,就别强迫自己写。”
想想杨晓升说得对啊。写作是为了独自的快乐,是身体本能的需要。
就这样,我开始了时隔近三十年的写作。大体上我只写我生命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经验。
打开电脑后,内心的伤感宛如矗立在内心一隅的某种摆设,形容为花瓶也可以。而文字则像对所有过去的一种抚摸。
我得出的理论是:我写作是因为我伤感。
《寅次郎》在《北京文学》发表了。无疑这一次发表成了我日后写小说的垫脚石。那个时候,写作的冲动带着伤感,影子般向我伸展过来。一段生活会结束,但生活本身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
写作的时候好像亲吻自己的痛苦,那就这样恢复写作好了。
伤感哗哗地流,想收也收不住。用一年半写的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发在2019年第6期的《收获》杂志。小说里很多地方提及了这篇散文中所说的伤感。发表后那段日子的感觉,好像自己由一只小毛毛虫变成了美丽的蝴蝶。伤感被写作彩色化了。
之后我又写了中篇小说《百分之百的痛》,除了《思南文学选刊》和《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选载了。这时候我觉得伤感跟写作简直就是双胞胎。



链接:这本由老舍先生在1950年创办的杂志——等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