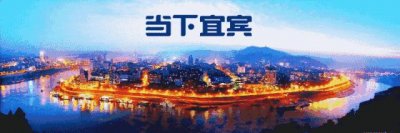老韩讲了一个故事:大炕
老韩讲了一个故事:大炕







在那个时代的北方,居家过日子,如果没有一盘点火就热,不倒烟而且好烧得热炕,那他家的日子才叫苦呢。一个人在外面无论遭遇多么心灰意冷的事情,包括被整肃、被批斗。回到家里,一摸炕是热的,心里就会生出一股热乎气儿,萌出一丝暖意和一点希望。如果一摸炕冰拔凉,那真是一种彻骨之寒,首先心就凉透了。炕,是北方人最后的温暖的窝。
炕并非是穷人的专利。在北方,过去有钱人也睡炕。只不过穷人铺的是炕席,富人铺的是厚厚的毛毡和炕毯。听父亲说,在解放前的雁北,能铺起炕席的人家也很少,人们用蛋清和一种捣得烂烂的草汁拌在一起将土炕抹得光鉴照人。那时一家人也不见得有一床被,多数人成晚地在炕上和衣而卧,因炕烧得热而辗转反侧,像烙饼一样不住地翻身,地上两口大缸里腌满了酸菜,漫长的冬季就是这样挺过来的。
六七十年代的雁北,一般社员家炕上只有一块席子。大队干部家也许有块棉花毯子,公社书记家才有炕毯。也有连席子也铺不起的人家,炕面用牛皮纸糊。所谓的牛皮纸就是工地上用完的洋灰袋子。一层一层地糊,糊成东北老太太纳鞋底的袼褙一样厚厚的一层。再在牛皮纸上刷上油漆,亮堂、干净。但也有弊病,病在掏炕。一旦掏炕,就须割开一块。本来很好的工艺,变得不再齐整。虽然可以沿着割开的地方再糊上一条,可感觉上总有些缺憾。再后来,又时兴铺纤维板。记得刚开始卖纤维板的时候,许多人家的男人大张大张地往家里背,仿佛家里又添了大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纤维板也须刷油,否则沾了水会起泡。但刷了油,滑得像镜子,小孩子们常在上面摔跟头。
听同事说,1980年9月,他们在河南林县施工,住在老乡家里。那里有许多人家炕上铺的是油毡,油毡就是那种建筑物防水用的材料。一天,他穿着衬衫午休,醒来时咋也坐不起来,好像后背被大炕紧紧地吸住。后来解开扣子手臂从袖子里脱出,才得以起身。起来后才发现,因为炕热,油毡融化,衬衫与油毡竟粘在了一起。
炕席也罢、裱糊也罢、油毡也罢。包括后来的纤维板,都改不了火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十冬腊月,后背被烙得滚烫,胸前却仍然冰冷。虽然说家暖一盘炕,但不少人家早晨起来还需要砸冰取水,因为缸里的水后半夜就被冻住了。
要烧炕,家里就免不了灰尘。煤灰在空气中飞扬,落得到处都是。擦炕是女人们的一项例行家务事,跪在炕上,子撅起,手抓一块破布,从左至右地擦抹,很是吃力。只要一天不擦,炕上一偎,黑色的裤子就会变白,白色的裤子就会变黑。改革开放之后,有的人家铺上了人造革,好像生活又高级了一些。但许多女人的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啥时不用再擦炕了?
那时,不管去谁家,炕头上常常放着正在发酵的面盆。盆边卧着一只逮耗子的老猫,看上去温馨而舒畅。后炕靠墙垛着大花面的被褥和枕头,雁北人叫盖窝垛。盖窝垛边上是扫炕的笤帚疙瘩、烟笸箩及针钱笸箩。
人口多的人家,盖窝垛得能挨住仰尘。叠盖窝、码盖窝垛可是个技术活。好比瓦工垒墙砌砖把角,低于七级的技工闹不了。乡间人们评价年轻媳妇儿干净利落会打理家,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这家的盖窝垛是否整齐。我的表嫂是得胜堡头等的巧媳妇儿,她家的盖窝垛只有半人高,叠得那叫一个整齐,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外面苫着一块红条白格的市布,远看就像一个小戏台。表嫂白天不让娃娃们上炕。娃娃只要一上炕,就伸胳膊踢腿,没有五分钟就把盖窝垛弄塌了。然后连人带盖窝一起滚蘸到炕中央,表嫂气的手提笤帚疙瘩满炕追着打
盖窝垛的功能很多,三舅患肺痨时,晚上平卧着喘不上气来,必须身靠盖窝垛半仰着,才能打个盹。被窝垛还是娃娃们藏掖东西的好地方。那年,五舅家吃油糕,五舅最小的儿子明奎,在盖窝垛里塞了五个油糕。至晚,五妗妗铺炕时抖活出来,滚得满炕都是。不用问她就知道是谁,恨不得把明奎按住杀了。
炕头离锅台近,比较热乎,是冬天家里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招待客人的雅座。贵客进家,主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快脱鞋上炕!棉袄一脱,棉帽子一摘,脱鞋上炕。盘腿坐定,主人递过烟笸箩,挖上一锅子,划根取灯儿点着,舒缓地抽起来。火炕烫屁股,不一会儿,浑身就热了。
主人招呼客人上炕,是那时最热情的习俗。从能否“脱掉鞋子,坐到炕头上”便能看出来客与主人的远近亲疏关系。睡席梦思则不成了,女主人总不能让客人:“上床哇,上床哇!”那不成体统。
炕头,—般来说是个尊位。长辈睡炕头,中间睡女人孩子,后炕是青壮年。只有来了尊贵客人的时候,热炕头才会让给客人睡,其他人依次都往后炕挪。所以,睡觉让炕头成了一种礼遇。另外,热炕头也是考核是否幸福的一个指数。来串门儿的人,进家都要习惯性地伸手摸摸炕头热不热,炕头热乎说明日子过得不赖,若炕头冰凉,说明这家人不是穷就是懒,很让人看不起。
“家暖一盘炕”,炕是一家之中心。人们串门走亲,炕上坐稳,才开始叙长道短。冬季,若你刚从寒冷的远处进来,立刻会爬上炕,把手塞在屁股下取暖;或把脚伸出来压在别人的屁股下,须臾,一股痒酥酥的暖意便通过肌肤,驱赶走哆哆嗦嗦的冷意。
雁北青年男女找对象,首先是媒人把小伙子带到女方家相亲。小伙子如果看上了姑娘便主动脱了鞋上炕盘腿坐在那里,一副自家人的姿态。姑娘如果也看上了小伙,就会害羞地躲在妈妈身后。
雁北有民谣曰:窗台上猫圪蹴,炕头坐的老两口,后炕枕头摞枕头,新媳妇炕上来梳头……节奏明快、韵味十足、句句不离炕头,可见老百姓对炕头的喜爱之情。
炕①是过火的,所以炕字是火字旁。有人以为炕是土做的,炕字自然为土字旁。我的大学同学付祺是上海人,那年他来内蒙古兴和插队,安顿下后就给家里写信说: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晚上一起睡在大“坑”上一点也不冷……爹妈看完信后,声泪俱下:我儿咋就睡在大坑上呢?还不冷?是不是我儿去了没什么技能,就挖大坑呀?那大坑有多深啊,掉下去咋办?第二天起来问邻居,邻居看完信说,你孩子说的是北方的大“炕”,写错了……
炕上打坐,是一种硬功夫,也是衡量一个人家教的最好验证。正规的坐法是盘腿压脚,这种坐姿是南方人难以模仿的。当然这种坐姿也是一种折磨,在雁北也只有大岁数的老人才有这种功夫。年轻人往往嫌腿麻脚疼,坚持不了片刻。
那时,一家两代人睡在一条炕上也是常有的事情。入夜,尿盆子就摆在地上。公公尿尿长驱直下;婆婆尿尿稀里哗啦;儿媳尿尿是怎样的局促与不安,没有任何其他动静可以为其遮掩。如果家里人口多,晚上下地尿完,上炕找不到睡觉的空隙也是常有的事情。
从我有记忆起,得胜堡的人都没有内衣。晚上睡觉,女人也许穿件红主腰子,男人几乎全部都是裸睡。许多人家两代人睡在一条顺山大炕上,月光如水的晚上下地尿尿,几无隐私可言。
记得四十多年前的一天,20岁的我去包头召潭火车站送站。把朋友送上火车,正要离去,看见站房外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娘吃力地拎着两个大提包,我见状便上前帮助她拎包,大娘告诉我,她家就在火车站五里外的赵家营子,求我送她回家。
我帮大娘拎着包一直把她送到家里,大娘的家里有老伴和一个20来岁的漂亮闺女,那妹子非常热情地给我沏茶。大爷便和我唠起了嗑,说他的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闺女都成家了,现在就老姑娘在家。大叔得知我在电建公司工作,便描述起多年前电建公司派人到他们生产队帮助他们更换变压器的情景。
坐了十来分钟,我欲起身告辞,但大爷大娘都拉住我不让走。大爷安排妹子赶紧炒菜,说要我陪他喝两杯。妹子麻利地炒了一个花生米,一个大葱炒鸡蛋,半盆子酸菜粉条,一盘土豆丝,我于是就和大爷对饮起来了,我那天只喝了二两就有些醉了。
后来我再次要走,大爷一家仍然执意挽留,我只好在他家住下了。当晚,大炕上四套被褥依次摆放,大爷旁边是大娘,大娘旁边是妹子,妹子的旁边是我,相互之间的距离约有50厘米左右。由于喝了酒,我躺下就睡着了。大约午夜时分,朦胧中觉得好像有谁踢了我一脚,我醒来后,发现是妹子的脚伸进了我的被窝,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她的腿。我的心急速地跳动着,后半宿怎么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天一亮,我便回单位上班了。这就是我在包头城中村睡炕的经历。
表哥说他也遇过类似的事情,一年他去五台洼帮人家老母猪接生,那天遇到难产弄到很晚,回不了堡子了,那个老乡很热情地请他睡自家的大炕。他睡左边,老乡睡中间,老乡的媳妇睡右边。睡至半夜,老乡被人喊起来打麻将,临走时在他和女人之间横了根柳木棒,说:“你是念过书的人哦!”然后就出门了。
表哥和老乡的媳妇睡在一条炕上,中间隔着一根柳木棒,俩人脑袋转过来,目光相遇。据表哥说,看到那女人眉目传情,吓得赶紧闭眼翻身,大气也不敢出。一夜都不安稳,心里跟猫抓一样。
天蒙蒙亮时,老乡回来了,仔细端详炕上的柳木棒,发现纹丝未动,挑起大拇指说:“你小子不愧是读过书的人!起来,咱俩抬点酒喝!”
炕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尤其在农村漫长的冬季,人们的生活圈子大多限于炕上。年轻媳妇们团坐在一起,拉着家常做针线活。补袜子、纳鞋底、搓麻绳、剪窗花。老年人则坐在一起,听见多识广的人说书、古。历史、民俗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在口头流传。总之七钩八扯、云苫雾罩,有说不完的话题。炕热了,坐不住了,用双手交替在屁股底下垫着,还是舍不得欠屁股离开这个热炕头。
相对于前述的“雅”,许多男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俗”,那就是喜赌。冬闲时,聚集在大炕上,用纸牌、骨牌、麻将,进行各种形式的赌博。因此在旧时,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女人们四处寻找聚赌的丈夫回家。
炕头还能发面、生豆芽,是保温箱也是暖床。过大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炕头上都会摆上几个蒙着棉被的瓷盆子、瓦罐子。
热炕头还能治病,炕头上趴一趴是雁北母亲们万能的治病绝招。肚子疼了,炕头上趴一趴;腰腿疼了,炕头上烙一烙。缺医少药的年代,母亲们的这一招,十分灵验、屡试不爽。
娃娃们喜欢趴在热炕头上写作业,写着写着,毛头小子长成了愣后生,丫头片子出落成大闺女。
炕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小孩子们往往在炕上活蹦乱跳,开心极了。大人们诈唬孩子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别跳!跳塌了炕板子,去哪睡圪呀?”
炕板子因为是土坯的,所以硬度不够。尤其那会都是一家老小经年累月地睡在一张炕上,土坯到疲劳极限时,就开始松散,最终有一天支撑不起就被压塌了。有乡谚曰:“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大概意思是说,一开始顺风顺雨的人不一定厉害,那些前期不顺而后时来运转的人才真的强。
听五舅说,刚打倒四人帮那年,临近新荣区煤矿的一个村子,有一户人家大约在一天凌晨时分,老汉跟老伴正在睡觉,突然被轰隆隆的声音震醒了,然后就感觉炕沉了下去,自己和老伴也顺着下陷的炕歪了下去,发现危险的他们赶紧爬了起来。“幸好爬起来的快,要不现在人都不在了!”提起当日的遭遇,那个老汉还是一脸的后怕和愤怒。第二天清理坍塌的炕时,老汉老汉发现,炕下面有一条约一米宽、深不见底的巨坑,“这坑怎么也得有十七八米深吧,没法填,虽然用几块石板盖住了,但仍然‘嗖嗖’地往外冒阴风。”老俩口快吓死了,赶紧躲到闺女家了。后来才听说,他们整个村子的底下已经被掏空,整个村子成了“危村”。
塌炕的事并不多,多数人家看见炕板子有些凹陷就更换了。常见的是,饭做得多了或柴禾加得多了,把炕洞里的烟油引燃了。不仅仅是烫得睡不下去,烫狠了,饼都能烙熟。炕面再热,因为是土坯,不能用水降温。只得在席子下垫几块木板,披着被卧蹲在炕角,等待炕温降下来再睡。冬天因烧炕燃着炕席、褥子、衣裳也是常有的事。半夜褥子着火了,急急忙忙地掀起来,不掀不要紧,“轰”的一声,火苗蹿出尺把高。待把火弄熄了,会惊出一身冷汗。
在中国广袤的西部,绝大多数穷苦的农户们都是靠它来熬过漫漫的冬夜的。用有限的柴草将厚厚的土炕烧热,蓄热后的土炕可以在一整夜缓缓释放出热量,衣衫褴褛,饱受了一天饥寒侵袭的人们能蜷伏在滚烫的炕上,简直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炕是谁发明的?真应该申请国际专利,无怪乎满足于小农经济的人们津津乐道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句话给人们的最温馨之处,仍然是热炕头,那是大铜床、席梦思不可替代的。
在土炕上睡久了,身上自然而然就会带有土炕特有的那种土腥味和炕烟味,这种味道从出生时起,就开始渗入我们每个人的血液,深入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对于离开家乡多年在外闯荡的人来说,土炕就是乡愁,土炕特有的那种土腥味就是乡愁的味道。风尘仆仆而来,爬上土炕,裹着被卧美美地睡一觉,细嗅着从土炕缝隙溢出久违的淡淡的煤烟味和土腥味,均匀地呼吸,就会忘掉外面所有烦恼和忧愁,辛苦与劳累,很快进入梦乡。
许多永远告别故土的人,心里却一直有袅袅炊烟在涌动。每当他们在这充斥着喧嚣与浮华的世界里,被生活的艰辛拷打着找不到方向,感到疲惫不堪,心慌意乱时,那温暖的土炕,就会浮现在梦境里。
现代人离火炕越来越远了。人们住进了高楼大厦,睡上了钢丝床、席梦思。但北方人却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现代的卧榻要比火炕柔软、有弹性,躺上去也挺舒服,但就是不如睡在炕上踏实。身底下的电褥子也能取暖发热,但那热显得很燥,像给人身上通了电流,远不如火炕来得自然温馨。火炕的暖如同温泉一般,先是人的背部被那亲切的温暖所浸漫。渐渐地,那股暖流向周身荡漾开来。最终,整个身体就像沐浴在暖暖的阳光之下,有种飘然微醺的感觉。尤其住楼房,未供暖或刚停暖时,家里阴冷如冰窖,会使我们更加怀念那盘热乎乎的火炕。
静下心来细思谋:床,是移动的炕;炕,是不动的床。不管床也好,炕也好,停息的都是人生。
“啥时候能再睡一睡热乎乎的火炕呢?”北方的中老年人在席梦思上翻来覆去睡不安稳的时候,常常这样想。
后记:
曾读过一本书,其中谈到1928年宋美龄在上海对来华访问的史沫特莱女士说:在中国的西部,人们都在一种叫炕上的东西睡觉,一家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如果有机会,真该陪你去看一看……
民国时期的学者章太炎曾提出废除北方睡大炕习俗,他的理由是:那么一个大通铺,父母、子女、妻妾睡在一起,“无所避忌,则德育无可言”;终日烧着火炕,屋子里闷热,让人头脑昏聩,所以“思虑不敏捷,则智育无可言”;又由于屋内高温燥热,让人筋络松弛,女人发育太早,“未及衰老,形色已枯,则体育无可言”。
按章太炎的说法,北方人睡火炕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北方人祖祖辈辈就这样生活,这样繁衍生息,一代一代地香火传承,那体形的高大壮实和生龙活虎的精神状态却是柔弱的南方人比不了的。这就说明,北方人睡炕不但有好处,而且好处相当大了,特别有益于人的发育成长。
当然,章太炎说的其中一条,确属事实,那就是在睡炕时,隐私得不到保障。但是,在民国以前,即使居住在老上海的普通市民们,同样也会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就寝,隐私也同样没保障。过去的北方农村比较穷困,儿子大了要结婚,又没有能力另建新房,只能在大炕中间拉上一道布帘当遮羞布,公公婆婆睡一边,儿子儿媳睡一边,当然没隐私可言。可是,如果把事情理解了,就觉得男女的事情本来就那么回事,只要看不见,就当没发生。到了现在,人们的日子好过了,再不富裕的家庭也有个东西屋,其中一间就是儿子儿媳的婚房。也就是说,条件允许了,人们也就讲究了。
在吊丧活动中,岚县一带还有一种“管炕”的习俗,即本家、邻里或亲友帮助丧家招待宾客的住宿和饮食。一般分三步进行,一是请炕。丧家根据宾客人数定出所需的炕数(一般每一炕家负责六至八人),然后略备水酒,请炕主前来议事,征得同意后,炕家就算定下来了。二是管炕,头一天祭祖结束后,就由总管分配炕员,抄出名帖交与炕家。炕家把宾客接到家中,烟酒茶饭款待。一般晚上吃面条,取亲戚往来长久未断之意。第二天,出殡后宾客要在丧家“坐老斋”,即吃殡饭。饭后再由炕家接到家中稍事休息,下午散客,炕家的义务也就完成了。第三步是谢炕,下葬后的第二天中午,丧家要设酒席酬谢炕家。谢炕完毕,管炕这一活动也就全部结束了。
管炕还有“干、湿”两种,以上所述叫“湿炕”,即连住带吃;而“干炕”,就是只管住,不管吃,事后也不谢炕。一般“湿炕”居多,“干炕”较少见。当地把这种活动作为一种互助性的活动,谁家也不计较为对方担负义务的多寡。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
注①:其实写作“火坑”也无错。《汉语大词典》“火坑”条曰:“火坑,亦作‘火炕’,北方人用坯或砖头砌成的一种床,底下有洞,可以生火取暖。”(作者 韩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