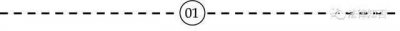中国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
中国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
口述 | 魏纪中(中国奥委会原副主席、秘书长,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
采访整理 | 杨玉珍
10年前的2008年8月,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人百年奥运的梦想终于在那一刻圆满成真。下面要讲述的,是两次申奥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图 视觉中国
邓小平说:“你们敢不敢申办一次奥运会?”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申办奥运会的想法?这还要从邓小平说起。
1974年,党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他复出后分管的第一件事正是体育,管的第一个政府机构就是国家体委。1974年2月的一天,邓小平听完国家体委主任王猛的工作汇报后说:“中国现在已经进了联合国,我看要把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提上日程,我们不能总在奥委会之外。”(在参加了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后,我国继续要求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在之后不久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虽然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但在国际奥委会中仍然出现了“一国两会”式的“两个中国”的现象。为坚持维护新中国尊严和领土完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1958年退出国际奥委会,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编者注)从这之后,我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及相应做法开始转变,谋求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成为工作重点。因为席位恢复之后,我们不仅可以参与奥运会,而且可以举办奥运会。当然,当时的目标首先是参加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并没有真正提上日程。
申办奥运会提上日程,是在1990年亚运会之后。1979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1980年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1984年开始真正大规模地参加奥运会,在当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拿到了15块金牌。到这一年,我国对体育的热情已经被充分点燃。也是从这年开始,我们确定并开始筹办1990年亚运会。本来1990年亚运会的主办方是日本广岛,后来我们跟广岛协商让我们先办,广岛同意了。当时我国就是想利用亚运会这个民间的主场外交来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让世界认识中国。
1990年7月,亚运会的筹备工作基本结束。7月的某一天,邓小平在国家体委和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来考察亚运会的准备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和亚运村的建设工程,对这些工程建设很满意。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我看这些工程建设都挺好,办个奥运会也差不多了。”接着,他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敢不敢申办一次奥运会?”可是当时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
1990年9月,我们的亚运会办得很成功,全世界反响都很好。闭幕式搞得也很隆重,很成功。闭幕式结束之后,所有参加闭幕式的演员和年轻志愿者都很激动,他们齐聚在工人体育场的草坪上欢呼雀跃,久久不愿离去。当时主管体育的国务委员李铁映走下主席台,来到演员及志愿者当中,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场面非常激动人心。铁映同志讲完之后,回到工人体育场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想起了小平同志的“申奥”之问。大家都说,是时候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了。最后铁映同志表示,我们先成立一个以国家体委和北京市为主的小组,对办奥运会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等研究结果出来后再做结论,这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次讨论之后,马上就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说是小组,其实就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刘玉令,一个就是我,当时我是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为了搜集情况,我们两个人就到有关部委去跑,外交部、财政部、发改委(当时称国家计委)等都跑了个遍。我们同这些部委的领导谈我们的想法,请他们帮忙看看申办奥运会有没有可行性。结果,所有这些部委都十分支持我们,不但支持,还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外交部说,外国运动员来华我们可以不要签证;财政部说,关于经费的话,这些钱我们还是能挤出来的;发改委说,结合五年计划,我们来帮你们解决相关问题。听到这样的答复,我们的信心大增。
之后,我们搜集整理了承办一届奥运会在硬件和软件以及财政和技术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同时也考量了在市政建设和城市现代化服务方面的各种要求,探讨了我们在电视转播和国际航空运力等方面的实际能力,评估了我们在环境保护和国民素质方面的问题,研究了改革开放方面的各种需求,并形成了一个初步的需求清单。接着,我们将清单呈给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北京市各有关部门,诚邀国内外专家提出意见。很快我们收到了最为集中的两点反馈: 第一,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们行;第二,大家都愿为此给予应有的支持和贡献。
根据这样的评估,国家体委与北京市人民政府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后达成共识,然后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同意北京市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在得到国务院的赞同和全力支持后,中国奥委会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了北京市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表决同意北京市迈出这勇敢的一步。
至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能回答小平同志的提问了,我们敢申办奥运会!
第一次申奥:众志成城,却功亏一篑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正式启动了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后,打出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之所以特别强调开放,是因为我们想通过奥运会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但我们很快就清醒地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因为对手都很强。
当时有五个城市申办,除了中国北京,还有澳大利亚的悉尼、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柏林、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五个城市在竞争过程中,实际上被分成两队,中国和伊斯坦布尔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一队;悉尼、曼彻斯特、柏林是发达国家,属于另一队。我们在舆论上很不占优势,西方的主流媒体一致反对中国申办。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倒是支持我们,可它们的声音在国际上基本听不见,因为当时的话语权都掌握在西方媒体手里。
一时间,北京要申办2000年奥运会一下子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世界不少媒体很快把它政治化了。我所说的“政治化”,是指不少政客纷纷发表议论,还有一些政治机构也作出决议,不是去支持他们各自的国家申办,却偏偏反对北京举办,而且只反对北京。我记得当时不仅有美国的参众两院表态反对北京,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我们是在为自己申办奥运会,这个行动惹怒了谁?我当时分析,可能是他们认为我们成功的概率太大了,因此要压一下,泼点冷水,可随后意识到问题可能并不这么简单。世界主流舆论方面几乎是一边倒,结论都是北京不合适。新闻媒体也整天追着要跟你争论,非让你认输不行。我当时是奥申委对外的秘书长,也就是新闻发言人,这样的身份使我成为新闻媒体的众矢之的。我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后边准跟着一伙媒体记者。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我反问北京奥运会侵犯了谁的人权,为什么不允许中国有自己的发展人权的道路。有些不太讲道理的人甚至把动物保护也扯到人权问题上,说什么中国人吃狗肉、吃猴脑、摘熊胆等,这些刁难我都得一一应对回答。其次是环境问题。不知从哪里来的国际统计说,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还总是拿悉尼的绿色与北京的“灰黑色”相比。对此我从发展上来说明,北京申办奥运会就是要在改善环境上下大力气,为百姓造福。当时与我并肩作战的,还有外交部的吴建民大使,他当时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应付西方媒体比较有经验。
不仅新闻界,来北京访问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时常会提类似的问题。当时国际奥委会有个规定,奥委会委员可以到申办城市访问,所以几乎所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到北京来了。委员大概不到100人,这足够我们应付。当时我是向国际体育界人士,包括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申办情况的小组组长,因为我能用英文或法文说。在基本情况介绍完之后的交流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譬如有人问,北京如果在下个世纪,也就是2000年后办奥运会是否会办得更好?如果你说会更好,他们就说,这次让给其他条件更好的城市办吧。于是我只能说,这个问题对其他四个申办城市也必然是同样的,他们是怎样回答的我想学习学习。我记得有一个荷兰委员,他跟我就某个问题辩论了三次,加起来有八个钟头。有些观点你如果说服不了他,他就会反复找你,一定要让你承认他的观点。对于亚非的委员还好办,对于西方的委员,做起工作来确实很困难,因为问题的症结在意识形态方面,而这不是靠你一两个人就能说服他们的。我们国内的发展那时刚刚起步不久,你给人家讲蓝图,但蓝图是很难说服人的,他们还看不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投票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北京的主要对手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和英国的曼彻斯特,它们都是英联邦国家,如果不争取提前淘汰其中之一,那么最后我们肯定要面临以一敌二的局面。北京如不能速胜,则越往后越不利,因为很少会有票再转移过来。
到了投票的时候,我们果真遭到了西方委员的联合阻击。一开始我们是多少票,到最后基本还是那些票,只有伊斯坦布尔在第一轮被淘汰后少数的票转移到我们这边来。而其他三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第二轮柏林下去之后,票都倒到曼彻斯特和悉尼去了,曼彻斯特下去之后,所有的票都倒到悉尼去了。
在2000年奥运会申办的过程中,国际奥委会还没有出台廉政规定,也就是说,委员们可以访问每一个申办城市,而申办城市也可以找一些理由去拜访委员进行拉票……
当时国际奥委会规定,每个城市可以去一个申奥代表团,规模200人左右。除了奥申委的大部分人外,我们的代表团还囊括了外交部、财政部、外经贸部和文化部等国务院部委以及我国数位有代表性的驻外大使、企业界和文艺界的明星。不仅如此,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名流也参加了代表团。我记得当时还去了个儿童合唱团,他们由老师带着,天天在蒙特卡洛的大街上唱歌,宣传北京申奥。
在蒙特卡洛的日子过得飞快,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如果做不到就会影响我们的票数。这样一来,我吃不好,睡不踏实,1.83米的大汉瘦得只剩下61公斤,当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虽然我们做了诸多准备,但到了投票那天,我们还是以两票之差败给了悉尼。
第一次申奥失败后,代表团很多人都伤心地哭了,何老(何振梁)也流泪了,因为他付出太多,也期望得太久了,眼看到手的东西,却以这么微弱的票数被剥夺了。我则是欲哭无泪。作为这届申办委员会对外的秘书长,我应该负责任。特别是当我知道我国人民的期望值那么高,我们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期望值那么高之后,更觉得这是自己欠下他们的一笔债。
现在再回过头来分析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大环境不允许,二是由我们国家当时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失败之后我们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申办奥运会并且获得成功这样的大事,对于中国而言,需要靠我们自身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靠我们国家不断树立起来的国际威望。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主场外交来宣传中国,但当时国际奥委会还主要掌握在西方人手里,亚非拉虽有一定的力量,但是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抗和扭转西方看法的程度。从内部来看,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1993年申奥的时候我们还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外国人看不懂,也看不清楚,他看不到你改革开放的成功,也看不清你改革发展的方向。虽然国内我们民众的情绪很高,都抱着很好的愿望,有决心把奥运会办好,但是人家并不理解,并不真正懂你。
当时我们还有一个错误观点,即认为亚非拉国家能帮我们进联合国,就也能支持我们申办成功奥运会。但是当时没意识到,联合国是一个政治性组织,而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只代表他个人,而不是国家和政府,国家只能给他们一些指导性而不是指令性的意见,所以政治性因素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第二次申奥: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第一次申奥失败使得全国上下都很失望,中国申奥的热情也受到很大挫伤。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表示希望中国申办2004年奥运会,但我们拒绝了。当时有个说法,原来是五星迎五环,现在变成五环求五星,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申奥失败确实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后来关于申奥的事情就一直拖着,一直到1998年底。
那时我已经退休离开国家体委,受命到中体产业集团当董事长去了。有一次国家体委党组叫我回去汇报集团的工作,汇报完之后要散会时,我顺便提了一句,我说:新世纪我们对于办奥运会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考虑?我把我的意见也和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说了,他说正在重新考虑,也和中央沟通了。
之后,中国奥委会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后,采取了积极态度,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包括北京在内,都表示了愿为此做出各自努力的积极态度。中央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势头和综合国力增强的情况,特别是受到我国国际威望大幅提高的鼓舞,也支持中国奥委会再次申办奥运会。
作为响应,中国奥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进行讨论,当时我还是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也参加了会议。经过表决,全会一致通过了由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议,并立即启动了申办工作程序。这个消息传出,顿时在国内外得到了热烈响应,与第一次申办时的情形相比,这次的响应更加充满信心,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北京确实具备了成熟条件。
作出这个决定后,中国奥委会把1993年参加过申办的一些人给请了回去。当北京市政府的一位领导找我咨询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再次“披挂上阵”、参与申办工作时,我简单思考后回答道:“谢谢领导还想到我。不过我认为,这次申办应有新面孔,让那些年轻的、能代表中国未来的新一代出现在前台。我确实老了,也许我的那些东西不再管用了,不宜再上第一线。不过我可以在幕后做些具体的实际工作。”因此,我进了申办委员会,但是没进申办委员会的工作班子,而是在组委会当执委。作为执委,我不用干很多具体工作,但要经常开会,发表意见。
当时我们的对手依然很强劲,五个申办城市分别是北京、巴黎、多伦多、大阪及伊斯坦布尔。巴黎的竞争力最强,那时候巴黎人脉关系极好,再加上“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就是法国巴黎人,巴黎经济实力也不差,所以是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这样,当时我还是感觉,北京胜出的可能性极大。通过与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接触,我明显感觉到了与上次的不同,我对北京的感觉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众望所归”。
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西方一些委员还是没有看得很清楚,仍认为我们的发展比不上它们,对中国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但亚非拉的委员们则不一样,他们能从自己国家所处的境况出发来审视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的变化他们体会尤深,认为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从中国的改革中他们看到了希望。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觉,亚非拉国家间的凝聚力更强了,这对我们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全会中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就在投票前几天,我特地去了一趟伊斯坦布尔,去找我的老朋友、国际奥委会委员、土耳其奥委会主席埃尔丁验证我心中的一些想法。埃尔丁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我们最早一起在国际排联工作,后来他离开排联,回土耳其当奥委会主席去了。我找他就是想摸摸底,看看中国这次的胜算有多大。到了伊斯坦布尔,他请我吃了一顿大餐,然后坦承地告诉我,中国这次希望很大,但不是第一轮胜出,可能要等到第二轮,因为第一轮很多人会投伊斯坦布尔的票。他向我解释说,伊斯坦布尔虽然知道基本没有希望成功,但每届的奥运会他们都会申办,因为他们国家有一条体育法律:只要他们申办奥运会,国家就可以拿出GDP的1%来支持体育事业,用这笔钱他们可以建设必要的体育设施。但是在这一次,政府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第一轮投票的票数要多于巴黎,否则以后就不让他们继续申办了。埃尔丁还告诉我,第一轮很多委员因为同情伊斯坦布尔,会把票投给他们,而第二轮中,这些委员就自由了,他们肯定会投给中国。
当我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国内的一些相关负责人时,他们不相信这种判断,认为我是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消息,与他们通过官方获取的信息不一致。他们认为,要么我们第一轮就胜出,要么我们最后和巴黎决战。但我还是充满信心,我坚信埃尔丁的分析是正确的。
之所以这么确定中国能赢,还跟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有关。在第二次申奥过程中,我经常会碰到第一次申奥时跟我争论过的委员,在跟他们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了。没有跟他们争论过的人可能没有这种体会,跟他争论过之后再跟他对话,会明显地感觉出他前后态度的变化。除此之外,我发现国际主流媒体记者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老给中国提一些刁难性问题,这一次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使北京的奥运会办得更好。
国际奥委会的投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随专机飞往莫斯科,住进了国际奥委会总部的酒店里。这一次,我不去找任何人,也不再去求他们给我们投上宝贵的一票,我就坐在酒店的大厅里喝咖啡。因为咖啡厅是一个信息的“交汇点”,除了能随时关注和打探申办形势,我还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人会主动来找我聊天。果不其然,主动来找我的人很多。我首先接触到的是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北京这次准没问题,别忘了请我们吃饭呀!”我也遇到过我们上次申办时明确没投北京票的几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们说:“嘿,魏,你记得吗,上次申办时我告诉你,北京等一等会办得更好。今天我看你们条件具备了!”你再听他们讲话,跟以前的语调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不说“我支持你们”这种话了,而是给我提各种如何能把奥运会办得更好的建议。我总共接触了四五十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四五十人基本上达到半数了,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分析,我的信心更足了。
中国奥委会领导还要我找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希望能稳住一些支持票,我安排了双方的会见。我方坚持一定要争取第一轮就出线,否则很危险,艾哈迈德亲王则笑着说:“放心吧,北京定会胜出的,第几轮并不重要。”这话与我在伊斯坦布尔听到的完全吻合,于是心里更踏实了。
7月13日这天终于来到了,根据抽签,北京的陈述安排在下午。清晨一大早,中央电视台就来车把我接到莫斯科河河边、面对乌克兰大饭店的一个临时安排的转播点,与国际电视中心中央电视台转播厅进行互动。这个任务为什么会落在我头上呢?就在我从伊斯坦布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给我打电话说,中央电视台要向全国直播7月13日莫斯科的现场投票,想请一位嘉宾协助解说,奥申委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都推辞,因此希望就落在我身上了。因为有对中国必胜的信心,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当天我的任务是对各个申办城市的陈述进行讲评,与我合作的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沙桐。那天风和日丽,陈述是9点开始,电视台从莫斯科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直播。我当时给自己定的基调是,要给中国人民信心,但是要逐渐升温,把调子一点点地拔高;要对各个申办城市尊重,绝不贬低任何城市。
对于北京的陈述,我主要是介绍背景,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北京陈述后,委员们开始提问,对其他城市只提两三个问题,对北京却一口气提了十几个。国内老百姓有点慌了,纷纷致电中央电视台,北京方面急电过来,要求对此进行解释,这个担子自然又落在我的肩上。我说,我认为是北京的陈述朴实、饱含真情,引起了委员们的共鸣,委员们才给我们提了这么多问题;从问题的提法上看,他们对北京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你要分析他提的是什么问题,是建设性的问题,还是刁难性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提的都是建设性的问题,意思是希望你能够拿到申办权,而且办得更好,这说明支持我们的人多了,而不是少了,是增加了我们的信心,而不是减少了我们的信心。
下午4点,委员们正式开始投票。这时我心里很平静。第一轮投票结果,大阪出局,我更坚信一切将在预料之中。第二轮投票结束,监票人把一个信封递给萨马兰奇。萨马兰奇对委员们说:“举办城市已经产生,投票结束,请委员们到宣布大厅等候宣布结果。”这时我异常兴奋,我心想,北京赢了!但我不愿剥夺全国观众充分享受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这两个字时的喜悦,因为他们期盼这一时刻已经太久太久了。只见萨马兰奇主席满面笑容地打开信封,然后从容平静地宣布了“北京”这两个字,宣布厅内顿时一片欢腾。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多年来欠下中国人民的债,这次终于由北京奥申委替我偿还了。
我们在莫斯科还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的庆祝活动。看到群众这么高兴,我们特别特别感动。第一次申办时,我们组织了3500人在人民大会堂,想着一旦成功就出来庆祝,但这一次是没有安排的,完全是大家自发的。当时有人问我是什么感觉,我说,世界上没有比看到人民发自内心的高兴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们干什么事都是要看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现在百姓这么高兴,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值了,我们这件事情是办对了。
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9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感谢关注我社官微:中国文史出版社